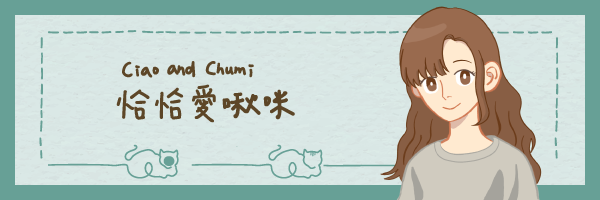

【父後七日 Seven Days in Heaven】2020| 其實一直深深記住在心底 |腦粉影評
人嘛~ 總是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當我們端詳著自己在鏡子的模樣已經青春不復返時,卻假裝忘記了支撐著我們成長的父母,是不是也不再是記憶中的模樣。不是我們不願意面對,而是我們不願意去面對,因為這一面對就好像有無限的聲音在你耳邊提醒你雙親也在時間的消磨下逐漸殆盡; 我們太害怕失去、害怕永遠的避風港會消失、害怕我們最熟悉的笑容和碎念,可能都成為一片雲彩,轉眼飄浮過眼前,所以我們不願意面對。《父後七日》藉由傳統文化的祭祀習俗讓家屬彷彿可以透過繁雜的手續搪塞滿原本該面對哀傷的時間,然而,當儀式逐步完成後,七日的荒唐行徑卻再也想不起來,更具體的是已經被壓抑了七日的悲傷,突然之間傾瀉而出。淚水是止不住的,這時候想要連根拔起早已深植腦海中的父親形象,才發現那都伴隨著成長的足跡,父親的大腳印和女兒的小腳印這樣左右左右的,我們是這樣踩著父親為我們開闢的康莊大道,所以才無所畏懼的前進。
父親林國源驟逝,阿梅隨即返回家鄉,連句話都還來不及好好的和父親說上,就已經是具冰冷的遺體。阿梅和哥哥大志兩個年輕人,誰也不懂得該如何操辦一切,還好父親生前好友阿義主動幫忙,全部才算是打點齊全了。台灣五光十色的喪葬習慣,卻帶領阿梅進入一趟匪夷所思又奇特豪邁的特殊之旅。『死亡』是一件總讓活著的人摸不著頭緒的事情,因為亡者不可能將自身經歷傳授給還在活著的人,所以我們利用各種方法將死亡包裝起來,傳統的、華麗的、西方宗教的…等等。可是仔細想想,一個人活著五六七八十年的一生,居然只需要短短的七日就足夠? 在《父後七日》的電影作品中,阿梅有兩種悲傷,一是道士阿義叔隨喊隨到的大哭不捨、另一是當阿梅真正有時間放空下自己後的真實的悲傷。父親的威嚴和疼愛僅僅一線之隔,學生時間嚴厲的要阿梅好好唸書,騎乘著一輛老野狼接送著阿梅的學生生活,那時候的阿梅青澀的單純,坐在父親身後,以為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家庭歸屬感; 而今,阿梅騎著自己的小綿羊,將父親的遺照畫框揹在身後,父親在外甥小莊的幫忙下,把舊時期的照片人工修改成一幅適合擺設在靈堂的樣貌。相片中的父親笑的燦爛,因為原本是開心拿著麥克風唱歌的姿勢,可是左鄰右舍不大滿意,說這未免太輕浮,才讓小莊把麥克風的地方修改成一把花束,似乎這樣就符合民意了。這時候阿梅才想起來在某一年生日的時候,也是一次放學回家的途中,父親緩緩將野狼停在路旁後,再神秘兮兮的從車廂拿出一顆粽子給自己,那時候阿梅大笑著說:「哪有人生日吃粽子啦」但像是順從父親的意思般吃的乾乾淨淨。那時候還需要坐在父親身後的阿梅,現在好像一夜長大了,換她揹著父親在同一條馬路上。
《父後七日》是部讓人有時候忍不住笑了出聲,卻讓每一道笑聲都被計算著刻畫在心裡,因為不可思議的喪葬儀式在經由阿義和阿琴的合作努力下,居然發展成為殯葬綜藝事業,花團錦簇的告別式、一堆不知從何而來的鄉長、議長、立委都好似真的與亡者是相處了半輩子的好友般,琅琅上口的說著亡者如何如何又善良又重情義,彷彿只有透過這些階級人士,才能讓原本只是在夜市擺攤賣CD的林國源身價更上漲一階。反倒是阿梅在『七日』之後又恢復空中飛人的職場生活,她忙碌的穿梭著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之中,時間緊湊的讓她『忘記』父親過世了這件事實,直到某次她在機場吸煙室大口吐著煙,內心裡突然有一個聲音提醒自己要記得在飛機上幫父親買黃長壽,那一刻,回憶翻攪著腦海,阿梅才真正認清父親已經過世的事實,她蹲坐在角落、手裡拿著還沒抽完的香煙,哭到不能自己…
轉貼原著散文 :
今嘛你的身軀攏總好了,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
葬儀社的土公仔虔敬地,對你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這是第一日。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身體的管子和儀器已經都拔掉了。僅留你左邊鼻孔拉出的一條管子,與一只虛妄的兩公升保特瓶連結,名義上說,留著一口氣,回到家裡了。
那是你以前最愛講的一個冷笑話,不是嗎?
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要分辨一下啊,有一種是有醫∼有醫∼,那就要趕快讓路;如果是無醫∼無醫∼,那就不用讓了。一干親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的時候,往往只有我敢挑戰你:如果是無醫,幹嘛還要坐救護車?
要送回家啊!
你說。
所以,我們與你一起坐上救護車,回家。
名義上說,子女有送你最後一程了。
上車後,救護車司機平板的聲音問:小姐你家是拜佛祖還是信耶穌的?我會意不過來,司機更直白一點:你家有沒有拿香拜拜啦?我僵硬點頭。司機倏地把一張卡帶翻面推進音響,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那另一面是什麼?難道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知道我人生最最荒謬的一趟旅程已經啟動。
(無醫∼無醫∼)
我忍不住,好想把我看到的告訴你。男護士正規律地一張一縮壓著保特瓶,你的偽呼吸。相對於前面六天你受的各種複雜又專業的治療,這一最後步驟的名稱,可能顯得平易近人許多。
這叫做,最後一口氣。
到家。荒謬之旅的導遊旗子交棒給葬儀社、土公仔、道士,以及左鄰右舍。(有人斥責,怎不趕快說,爸我們到家了。我們說,爸我們到家了。)
男護士取出工具,抬手看錶,來!大家對一下時喔,17點35分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能說什麼?
好。我們說好。我們竟然說好。
虛無到底了,我以為最後一口氣只是用透氣膠帶黏個樣子。沒想到拉出好長好長的管子,還得畫破身體抽出來,男護士對你說,大哥忍一下喔,幫你縫一下。最後一道傷口,在左邊喉頭下方。
(無傷無痕。)
我無畏地注視那條管子,它的末端曾經直通你的肺。我看見它,纏滿濃黃濁綠的痰。
(無病無煞。)
跪落!葬儀社的土公仔說。
我們跪落,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你了。你穿西裝打領帶戴白手套與官帽。(其實好帥,稍晚蹲在你腳邊燒腳尾錢時我忍不住跟我妹說。)
腳尾錢,入殮之前不能斷,我們試驗了各種排列方式,有了心得,折成L形,搭成橋狀,最能延燒。我們也很有效率地訂出守夜三班制,我妹,十二點到兩點,我哥兩點到四點。我,四點到天亮。
鄉紳耆老組成的擇日小組,說:第三日入殮,第七日火化。
半夜,葬儀社部隊送來冰庫,壓縮機隆隆作響,跳電好幾次。每跳一次我心臟就緊一次。
半夜,前來弔唁的親友紛紛離去。你的菸友,阿彬叔叔,點了一根菸,插在你照片前面的香爐裡,然後自己點了一根菸,默默抽完。兩管幽微的紅光,在檀香裊裊中明滅。好久沒跟你爸抽菸了,反正你爸無禁無忌,阿彬叔叔說。是啊,我看著白色菸蒂無禁無忌矗立在香灰之中,心想,那正是你希望的。
- 第二日。我的第一件工作,校稿。
葬儀社部隊送來快速雷射複印的訃聞。我校對你的生卒年月日,校對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的名字你的族繁不及備載。
我們這些名字被打在同一版面的天兵天將,倉促成軍,要布鞋沒布鞋,要長褲沒長褲,要黑衣服沒黑衣服。(例如我就穿著在家習慣穿的短褲拖鞋,校稿。)來往親友好有意見,有人說,要不要團體訂購黑色運動服?怎麼了?這樣比較有家族向心力嗎?
如果是你,你一定說,不用啦。你一向穿圓領衫或白背心,有次回家卻看到你大熱天穿長袖襯衫,忍不住虧你,怎麼老了才變得稱頭?你捲起袖子,手臂上埋了兩條管子。一條把血送出去,一條把血輸回來。
開始洗腎了。你說。
第二件工作,指板。迎棺。乞水。土公仔交代,迎棺去時不能哭,回來要哭。這些照劇本上演的片場指令,未來幾日不斷出現,我知道好多事不是我能決定的了,就連,哭與不哭。總有人在旁邊說,今嘛毋駛哭,或者,今嘛卡緊哭。我和我妹常面面相覷,滿臉疑惑,今嘛,是欲哭還是不哭?(唉個兩聲哭個意思就好啦,旁邊又有人這麼說。)
有時候我才刷牙洗臉完,或者放下飯碗,聽到擊鼓奏樂,道士的麥克風發出尖銳的咿呀一聲,查某囝來哭!如導演喊action!我這臨時演員便手忙腳亂披上白麻布甘頭,直奔向前,連爬帶跪。
神奇的是,果然每一次我都哭得出來。
第三日,清晨五點半,入殮。葬儀社部隊帶來好幾落衛生紙,打開,以不計成本之姿一疊一疊厚厚地鋪在棺材裡面。土公仔說,快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睏哦。我們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睏哦。(吸屍水的吧?我們都想到了這個常識但是沒有人敢說出來。)
子孫富貴大發財哦。有哦。子孫代代出狀元哦。有哦。子孫代代做大官哦。有哦。念過了這些,終於來到,最後一面。
我看見你的最後一面,是什麼時候?如果是你能吃能說能笑,那應該是倒數一個月,爺爺生日的聚餐。那麼,你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無從追考了。
如果是你還有生命跡象,但是無法自行呼吸,那應該是倒數一日。在加護病房,你插了管,已經不能說話;你意識模糊,睜眼都很困難;你的兩隻手被套在廉價隔熱墊手套裡,兩隻花色還不一樣,綁在病床邊欄上。
攏無留一句話啦!你的護喪妻,我媽,最最看不開的一件事,一說就要氣到哭。
你有生之年最後一句話,由加護病房的護士記錄下來。插管前,你跟護士說,小姐不要給我喝牛奶哦,我急著出門身上沒帶錢。你的妹妹說好心疼,到了最後都還這麼客氣這麼節儉。
你的弟弟說,大哥是在虧護士啦。
- 第四日到第六日。誦經如上課,每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早上7點到晚上6點。這些拿香起起跪跪的動作,都沒有以下工作來得累。
首先是告別式場的照片,葬儀社陳設組說,現在大家都喜歡生活化,挑一張你爸的生活照吧。我與我哥挑了一張,你翹著二郎腿,怡然自得貌,大圖輸出。一放,有人說那天好多你的長輩要來,太不莊重。於是,我們用繪圖軟體把腿修掉,再放上去。又有人說,眼睛笑得瞇瞇,不正式,應該要炯炯有神。怎麼辦?我們找到你的身分證照,裁下頭,貼過去,終算皆大歡喜。(大家圍著我哥的筆記型電腦,直嘖嘖稱奇:今嘛電腦蓋厲害。)
接著是整趟旅程的最高潮。親友送來當做門面的一層樓高的兩柱罐頭塔。每柱由九百罐舒跑維他露P與阿薩姆奶茶砌成,既是門面,就該高聳矗立在豔陽下。結果曬到爆,黏膩汁液流滿地,綠頭蒼蠅率隊占領。有人說,不行這樣爆下去,趕快推進雨棚裡,遂令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來,搬柱子。每移一步,就砸下來幾罐,終於移到大家護頭逃命。
尚有一項艱難至極的工作,名曰公關。你龐大的姑姑阿姨團,動不動冷不防撲進來一個,呼天搶地,不撩撥起你的反服母及護喪妻的情緒不罷休。每個都要又拉又勸,最終將她們撫慰完成一律納編到折蓮花組。
神奇的是,一摸到那黃色的糙紙,果然她們就變得好平靜。
三班制輪班的最後一夜。我妹當班。我哥與我躺在躺了好多天的草席上。(孝男孝女不能睡床。)
我說,哥,我終於體會到一句成語了。以前都聽人家說,累嘎欲靠北,原來靠北真的是這麼累的事。
我哥抱著肚子邊笑邊滾,不敢出聲,笑了好久好久,他才停住,說:幹,你真的很靠北。
- 第七日。送葬隊伍啟動。
我只知道,你這一天會回來。不管三拜九叩、立委致詞、家祭公祭、扶棺護柩,(棺木抬出來,葬儀社部隊發給你爸一根棍子,要敲打棺木,斥你不孝。我看見你的老爸爸往天空比畫一下,丟掉棍子,大慟。)一有機會,我就張目尋找。
你在哪裡?我不禁要問。
你是我多天下來張著黑傘護衛的亡靈亡魂?(長女負責撐傘。)還是現在一直在告別式場盤旋的那隻紋白蝶?或是根本就只是躺在棺材裡正一點一點腐爛屍水正一滴一滴滲入衛生紙滲入木板?
火化場,宛如各路天兵天將大會師。領了號碼牌,領了便當,便是等待。我們看著其他荒謬兵團,將他們親人的遺體和棺木送入焚化爐,然後高分貝狂喊:火來啊,緊走!火來啊,緊走!
我們的道士說,那樣是不對的,那只會使你爸更慌亂更害怕。等一下要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我們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 第八日。我們非常努力地把屋子恢復原狀,甚至風習中說要移位的床,我們都只是抽掉涼席換上床包。
有人提議說,去你最愛去的那家牛排簡餐狂吃肉(我們已經七天沒吃肉)。有人提議去唱好樂迪。但最終,我們買了一份《蘋果日報》與一份《壹週刊》。各臥一角沙發,翻看了一日,邊看邊討論哪裡好吃好玩好腥羶。
我們打算更輕盈一點,便合資簽起六合彩。08。16。17。35。41。
農曆8月16日,17點35分,你斷氣。41,是送到火化場時,你排隊的號碼。
(那一日有整整80具在排。)
開獎了,17、35 中了,你斷氣的時間。賭資六百元(你的反服父、護喪妻、胞妹、孝男、兩個孝女共計六人每人出一百),彩金共計四千五百多元,平分。組頭阿叔當天就把錢用紅包袋裝好送來了。他說,台號特別號是53咧。大家拍大腿懊悔,怎沒想到要簽?可能,潛意識裡,53,對我們還是太難接受的數字,我們太不願意再記起,你走的時候,只是53歲。
我帶著我的那一份彩金,從此脫隊,回到我自己的城市。
有時候我希望它更輕更輕。不只輕盈最好是輕浮。輕浮到我和幾個好久不見的大學死黨終於在搖滾樂震天價響的酒吧相遇我就著半昏茫的酒意把頭靠在他們其中一人的肩膀上往外吐出菸圈順便好像只是想到什麼的告訴他們。
欸,忘了跟你們說,我爸掛了。
他們之中可能有幾個人來過家裡玩,吃過你買回來的小吃名產。所以會有人彈起來又驚訝又心疼地跟我說你怎麼都不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會告訴他們,沒關係,我也經常忘記。
是的。我經常忘記。
於是它又經常不知不覺地變得很重。重到父後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飛往東京的班機上,看著空服員推著免稅菸酒走過,下意識提醒自己,回到台灣入境前記得給你買一條黃長壽。
這個半秒鐘的念頭,讓我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直到繫緊安全帶的燈亮起,直到機長室廣播響起,傳出的聲音,彷彿是你。
你說: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