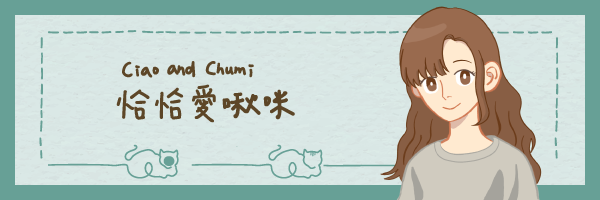

‖美國女孩‖American Girl‖

// Q: 既然導演您經歷過這樣的歷程,未來假使您的孩子的話,還會讓孩子也走上這條路嗎? //
這是在散場後我獨自請教導演的問題。導演侃侃而談地表示,就是因為自己經歷過這場台灣、美國、台灣的輾轉,她會學習著與孩子溝通,而非同電影故事中或是該年代的父母般什麼也不說的將孩子哄著哄著成為事實。
當導演說「哄著哄著成為事實」時,我回想起了我的童年。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家庭裡重男輕女的案例比率是多少,但我很清楚知道這在我奶奶眼中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也因為如此,我是外婆帶大的。一直到即將上小學的年紀,有一天我爸爸難得的出現在外婆家對我說:「我帶你去看兔子,那是在奶奶家附近的學校裡有養很多兔子哦…」。或許是小孩子敏感地嗅出空氣中不安穩的氣息、也或許是爸爸出現的很意外、或是我真的看見了外婆眼眶紅紅的,我死命地抓緊鐵門大喊著:「我不要看兔子、我不要看兔子…」。但是小朋友的力氣哪掙得過一個成年男人,爸爸根本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就把我扛在肩上,我眼看著我被扛走了,我只能一直哭著和外婆說:「我很快就回來了、我很快就回來了」。然而事實上,我沒有很快就回來了。爸媽擔心我一旦回到外婆家就沒再那麼容易被哄騙,硬生生的把我放在我完全陌生的奶奶家直到上小學。
後來我來才知道,那是因為爸爸很慎重地告訴自己的媽媽 (也就是我奶奶) 他們不會再生第二胎了,無論多想要男孩子,我奶奶必須接受只有一個孫女這件事情。
後面可想而知,重男為首的奶奶當然不會輕易地妥協,我和我媽媽的日子過得怎樣?…就是像八點檔那樣。
所以在《美國女孩》裡,姐姐芳儀對媽媽莉莉說:「我已經答應潔西要一起參加暑期夏令營」時,我發現了莉莉的眼睛神色匆匆,長大之後的『我』明白了,芳儀的願望再也不可能成真,『台灣』將成為她不明白的轉捩點。
//我沒有哭,但我想起了小時候//
映後阮鳳儀一上台便問觀眾們:「有哭的很誇張嗎?」,當下我的內心一陣困惑,無法理解這個問題是過往觀眾最常發生的情況嗎? 回頭看看其他觀眾,大部份的人還是泰然自若。阮鳳儀導演親切的像QA的主持人,頻頻和大夥分享著自己走過諸多映後的感受。影中的小妹妹芳安相形之下更顯得淡定許多,雖然年紀很小,但卻成熟的像個大人,有條有理地敘述著拍《美國女孩》的片場經驗以及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
//如果這是一場家庭革命,你想站在誰的角色?//
影中姐姐芳儀,在演講稿上寫著『影響我最深的人』是媽媽”恐懼讓我更恐懼、軟弱使得我更軟弱”。母女關係是一種鏡像理論,如同原生家庭般; 媽媽在對孩子說話時會說「我們」,而「我們」則是將孩子歸納為自己的一部份,沒有人對這項論點抱持著質疑。而觀眾們則從阮鳳儀導演半自傳的《美國女孩》中回憶到曾屬於自己童年時期最孤獨且無助的片刻。
//辮子V.S 妹妹頭//
在機場等待行李轉盤的時候,芳儀全然『美國風格』的辮子頭最為受到注目,那是一個自由體制下的產物,在相彷時代的台灣,那樣的髮型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尤其是中學學校。
老師說妹妹頭是為了讓女學生不需要費心打扮,只需要專注在學業上。只要沒有了可以梳扮的『標的物』心思就不會左右搖擺不定,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在藍祖蔚老師的評論中,芳儀的辮子之於小豆子的第六根手指 (霸王別姬) 一旦除去了便產生了自我認定的模楜感。
透過《美國女孩》中芳儀與芳安的對話:「我記得你最討厭每個周末都要剪優惠卷了!」以及芳儀對同學的對白:「我媽每天要我背20個英文單字」中可以明白,芳儀在最需要『落地尋根』的時期,先是被要求融入美國的生活環境後又被要求踏入台灣的填鴨式教學,頭好不容易洗完都吹乾了然後又被迫再洗一次,而這次她已經知道自己應該可以反抗,所以芳儀字字言語都針對著媽媽莉莉,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一切都是『被選擇』的『非自願的』。如同老一輩常會說的一句話:「小孩子有耳沒嘴。」意思是大人怎麼說聽就好了,不需要表達意見,更準確的說是『沒有發表意見的權利』。
//《美國女孩》想說的是什麼?//
父親在家庭分工下扮演的經濟支柱的角色,母親帶著小孩到美國生活,在那個『來來來,來台大; 去去去,去美國』的環境背景,芳儀、芳安就這樣隨著母親莉莉踏入一個陌生的國度,因為『去美國』是父母最大的夢想。但在終於融入了美國的生態圈後,芳儀與芳安又面臨了母親罹癌必須回到台灣治療的抉擇。芳儀、芳安因為是孩子,所以沒有選擇的權利,她們依賴著母親與父親的想法去了又回來。好不容易適應的環境就這樣再重來一遍,言語上的隔閡事小、文化背景差異的事大,在同學眼中的『美國人』芳儀,其實是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完全亞洲人的面孔,卻三言兩語間穿插著英文。同學們對芳儀不需要學習外來語英文感到羨慕、老師對芳儀中文一竅不通感到不可思議,再伴隨著母親莉莉接受癌症化療後的諸多不適感,是分身乏術。但莉莉依舊能做好每一日的早餐,讓一家四口團聚在餐桌前,這也讓人感歎母愛的偉大。
父親的角色是許多觀眾覺得突兀的融合。畢竟按常理來說,孩子長時間與母親共處、父親獨自留在台灣,為什麼父女的感情與母親相比格外融洽? 父母親的內心都會有想『彌補』的想法,例如父親宗輝一面大聲喝斥著芳儀要一台單車,把自己當提款機,卻又在另一晚帶著一輛嶄新的單車回家給芳儀; 或是妻子莉莉交代替芳儀買個書桌,父親又在芳儀的鼓吹下買了梳妝台…父親宛如芳儀與母親間的海綿墊吸收著所有的不愉快,一點一滴、一點一滴直到再也無法吸進更多之後,在一次芳儀與母親的爭吵時奮而抽了一記耳光在芳儀稚嫩的側臉上。
《美國女孩》像是家庭革命又像是社會的產物,每位觀眾都可以在相同的一個故事中得到與自身某部份相同的感受; 在阮鳳儀導演與觀眾分享自己童年記憶中最難過的一個關卡時,同時也從觀眾回饋中得到療癒; 當然,這也會是身為觀眾的我們從《美國女孩》中一併獲得的解脫。


